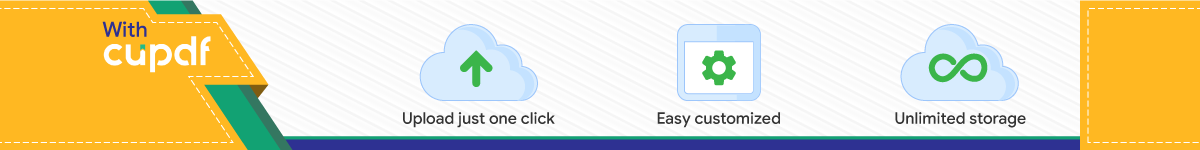

□贾炳梅
2019年7月15日08版 副刊·乡土
编辑 张喜梅 美编 李春梅 校对 张喜梅
乡土,是一代又一代人对过去岁月的怀想,是四合院夏日里树影婆娑的荫凉,是农舍屋顶上随风而逝的缕缕炊烟,是村外河道里曲曲弯弯的泉水叮咚,是春季田野里鸟儿清脆的鸣唱……乡土,活在你、我、他的记忆中。如果你的记忆中,还萦绕着有关故土的人或物,请用文字记录下来一起共享。
文体要求:散文或随笔 字数:1500~2000字来稿请寄:[email protected]联系人:张喜梅联系电话:69728984
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文字里的乡土
奶奶的捻线陀螺
奶奶的捻线陀螺
藏在野堰里的夏趣□ 王丕立
小时候生活在物质匮乏的乡村,大人小孩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奶奶和妈妈手工缝制的。纺车、织布机、捻线陀螺、线拐子是奶奶房子里常见的工具。最让我难忘的,是奶奶的捻线陀螺。
奶奶的捻线陀螺是用木头做的,形状如现在人们健身用的哑铃一般,两端如拳头大小粗大,中间凹细,仿佛两只顶端连在一起的陀螺。中间凹细处打孔,穿一根五寸长的称钩般的硬铁丝当陀杆。奶奶的捻线陀螺因为常常使用,被磨得光滑锃亮,看不出木头本来的颜色而成了浅褐色。
大概因为那时候家里人口众多,每个人的衣服鞋子都需要一针一线缝制,奶奶和母亲、婶婶一直有忙不完的针线活。记忆里,奶奶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她的捻线陀螺和一大把搓捻好的蔴线,那个捻线陀螺随时都在奶奶手里旋转着,发出“嗡嗡”声响。
奶奶捻线的时候,会从提前就搓捻盘好的一根根麻线里抽出一根,在手指上粘点唾沫,将那根麻线捻一下,拴在陀杆的梢头上,把线陀提起来。奶奶左手提着陀线,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用劲一捻,捻陀就转忽地转起来。捻线陀螺稍稍斜着悬浮在半空里,自顾自旋转并微微晃动着,奶奶一边和邻里大妈们说笑着,一边不时在转动的蔴线上续上另一根麻线。不停转动的麻线不断地被续接着延长,直到奶奶高高举起的左手实在无法再升高,奶奶就会麻利地用右手按住捻线陀螺,转动着将捻好的线一圈圈盘到那个陀杆根部,再续蔴线,继续转动捻线陀螺。
一根细长的蔴线像春蚕吐丝一样,从她的手中长长拉出来。小巧玲珑的线陀在奶奶的手中快速地旋转,如一个用鞭绳抽起的陀螺,旋转再旋转。待到估摸着绕在线陀上的蔴线长度够捻一根麻绳了,奶奶就用右手大拇指很熟练地在线陀顶端凹槽处去除活结,重新拿起一根蔴线拴在陀杆上开始下一根……等到捻线陀螺中间凹陷处全部盘满粗细均匀的蔴线,甚至凸起如同弥勒佛大肚子时,奶奶会站起来,将刚刚盘好的最后一根麻线从捻线陀螺上取下来,将蔴线最中间挂在陀杆上,将两根蔴线逆时针转动,和成一根更加粗一些的蔴线。然后在蔴线的一端,奶奶很仔细地去掉一些,粘着唾沫用手继续搓捻得更细、更光滑,直到能让一根针穿过。这样一根根一米多长、粗细均匀的两股纳鞋底的蔴线绳就捻好了。
奶奶捻出来的蔴线绳均匀、光滑、结实。通常,一家老小的鞋底全靠这样的蔴线一针一针纳出来。软软的碎旧布糊成的鞋底,被蔴线绳密密麻麻地纳得很坚硬。白白的鞋底,黑色的鞋面……一双结实、舒服、透气的布鞋,常常离不开奶奶捻线陀螺旋转出的那一根根蔴线。而一双双用奶奶捻的蔴线做成的鞋子,则陪伴着我们走过了清贫时代。
如今,我们再也不用一针一线去做衣服鞋子,奶奶的捻线陀螺也早已闲置成记忆。而那个凝结着奶奶辛苦勤劳、孕育着我们成长、串联着我童年梦幻、转动出一家老小行走希望的捻线陀螺,却一直嗡嗡地萦绕在我的脑海……
老家的菜园里有一口野堰。儿时,那口野堰藏着满满的夏趣,逗引我整个夏天都围绕着野堰跑来跑去。母亲说那里面藏着一个妖精,勾去了我的半个魂儿。
野堰是老家的习惯说法,是指没给人提供饮水之用的堰。在没通自来水之前,我们都是挑堰塘水来吃、用。我家的菜园位置有些孤野,在西坡的最高处,园中有口面积近一亩的堰塘。因为远离人家,没有人从塘中取水饮、用,也没有人在里面洗衣、洗菜,只有母亲常常担水浇园。由于西坡是禁山,不容许人砍伐,葳蕤的藤蔓缠绕葱茏的树木,形成菜园天然的篱笆,两山排闼之隙,母亲安上一扇竹门作为园门。
炎炎夏日,园中池塘总是一泓碧水。由于浇灌方便,母亲的菜园总是风情无限,红的西红柿、辣椒,紫的茄子、苋菜,青的白菜、豆角、黄瓜,满园生气,看上去无不水汪汪的。
堰堤北角有一棵大樟树,像一把巨伞撑出一大片荫凉,树下有两条长长的青石板。我常常打开园门,邀请小伙伴们坐在青石板上。山顶风凉,汗流浃背、暑气难忍的我们,一到树下就息汗,感觉全身特别凉爽。
堰堤上有一排毛桃树,树上密密匝匝结满了鹌鹑蛋一般大小的桃子。我挽着母亲的竹篮,摘一筐毛桃,在池塘中摇几下,提上岸来,和小伙伴们绕竹篮围坐一圈,用家里的小铁剐,划拉掉皮。毛桃果肉已经开始泛红,吃起来肉质非常细嫩、紧实,酸酸甜甜味道特别长。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果蒂和果柄,铁剐一转,一个毛桃便已去皮,惊起小伙伴们一片欢呼声。我受到鼓舞,摘来园中红透的西红柿,砍来堰堤南角已黑穗的甜高粱,和小伙伴们大快朵颐。那些红玛瑙一般汁水丰富的西红柿,碧绿浸润的甜高粱梗,被我们拿在手中把玩良久,最后才当食品吃掉。它们的模样,早刻进了我们小小的脑海。
堵住了馋虫,我们从塘底用手挖出一团黄泥巴,在青石板上砸响炮。砸响炮很简单,首先像揉面粉一样把黄泥揉得绵软紧实,捏成碗口形状,碗口朝上用右手托起,迅速翻转手腕向下使劲一摔,“嘭通”一声响如放铳。在此起彼伏的响声中,我们内心的愉悦渐渐充盈起来。
日头偏西的时候,我们跃进池塘,洗净手上的黄泥,洗净脸上的泥点。胆大的胖儿,总是喜欢到水深的地方,用手扯动中央的浮萍。细长的蔓草茎上总缀有几个野菱角。野菱角有尖尖的四个角,拇指一般大小。咬开外面的红皮,里面晶莹如雪的果肉特别细嫩甜软。胖儿分给我们每人几粒。晚风中,我们唱着“打靶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去。
那口野堰藏住了我童年夏天的乐趣。长大后我才知道,野堰并不野,它是父母整饬的结果,是他们特意为我打造的乐园。
Top Re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