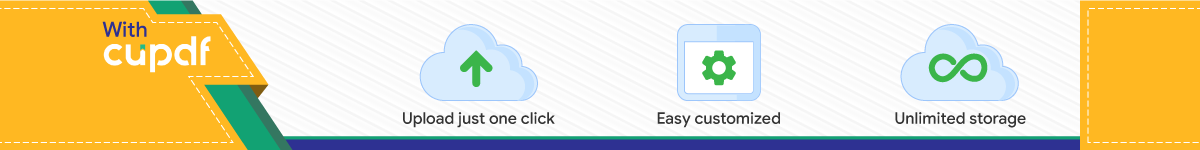

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老人天地88版版 ■2019年6月26日 ■星期三■版式设计:王玉娟 责任编辑:王玉娟■联系电话:2823695 邮箱:[email protected]
朝花朝花夕拾夕拾
亲亲 情情
晚晚霞霞
纪纪事事
儿时的几个伙伴聚会,不觉聊到童年趣事。小时候偷花生那件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别看我是女孩子,小时候可野了,上树捋榆钱,翻墙头,跳麦秸垛等等,比男孩子还淘气。
那时候家里虽然穷,但爹娘总教育我不能偷人家的东西。不过我总是不把他们的话当回事。春天拔葱,夏天偷杏,秋天摘石榴……小偷小摸,从没有被发现过。我一直为自己的聪明暗自得意。
有年秋天,我领着五岁的小弟弟吃过早饭就挎着篮子,拿着锄地勺到地里刨花生。主要是捡人家的漏,搜寻一上午篮子
底都没盖满。快晌午的时候,天空渐渐乌云密布,很快就要下雨的样子。有块地里一对夫妇正用起粪叉把花生根掘出地面。我计上心头,对弟弟说:“咱们不能空着篮子回家,先在地头的沟里趴会儿,等一下雨,地里的人走了,就去摘它一篮子。”弟弟当然没意见。
一会儿雨点子就如珠子般啪啪啪往下掉,那夫妻俩好像在争论什么,一会儿男人扛着粪叉走了,随后女人也跟着走了。等看不见人影了,我俩才从沟里爬出来,跑到地里放心大胆摘花生。我边摘边自鸣得意,说:“他们忙一夏,咱们忙一会,捡现成好吧?”小家伙一脸崇拜地直点头。
等把篮子装得满满的,我俩都成了落汤鸡,但心里想着回去可以吃到香香的煮花生就无比欢喜。
我和弟弟回到家,娘一边嗔怪我:“怎么才回来,你爹都出去找你们了!”一边让我们换衣服,洗手吃饭。
爹回来看到屋子里的一篮子花生问我:“花生哪来的?”
“捡的。”我头也不抬地回答。父亲提高了音量:“胡说!我们大人刨
一天也刨不了这么多,你们比大人还有本事?说实话,要不就准备挨揍!”
我依然嘴硬:“就是捡的,我们找的那块地落下得多。”
爹一把把我拽到身前,“啪啪啪”几个响脆的巴掌拍在我的屁股上,火辣辣地疼,我只好流着眼泪说出实情。爹让我坐到他腿上,问:“如果咱家地被人偷了,你咋想?”
“我会气死的,让我逮到肯定会揍他!”父亲笑了:“那你咋还去偷人家的呢?”我无语,不好意思地垂下头。父亲拉
着我的手说:“咱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不偷不抢,到你们这一辈也不能变。一会雨停了,咱给人送回去。”
雨一停,爹就提着那篮子花生带我找到人家地里。快走近的时候就听到那家女人在抱怨男人:“我说弄完再走,你不听,看看被人偷了这么多,咱辛辛苦苦白忙活!”男人也气得脸色铁青。我拉着爹的衣襟不敢再向前。爹拽着我走到夫妻
俩跟前,把篮子里的花生一股脑倒在人家筐里,说:“我闺女不懂事,摘了你家一篮子花生,我给送回来了。”然后又让我给人家道歉。
那夫妇看父亲实在,反倒不好意思了,又拿过我们的篮子给倒了不少,说:“给孩子煮着吃。”爹推辞不过,只好收下。站在一边的我惭愧不已,低头摆弄着衣角。
晚上,吃着煮熟的花生,爹又说:“记住,光明正大得来的东西才能吃得心安理得!”自那以后,父亲就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诚实的种子,后来我又把它种在儿女的心中,时刻牢记: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进院见菜绿,开窗闻花香。2017年我不在京秦高速机关舞文弄墨发挥余热后,在玉田城外过起了田园生活,居住的宽敞民宅有一个不小的庭院,足有3分多地可栽种。庭院东西是两道红砖墙,一棵老香椿树长得和房子一般高,像是在镇宅;两棵柿子树矗立两旁,柿子寓意着事事如意。院子中间是一条水泥路,能进小车,出人方便。水泥路西侧种的全是菜,主要有蚕豆、菜头、小葱、大蒜、豆角、茄子、黄瓜、辣椒、苦苣、番茄、韭菜、油菜、莴苣菜、生姜等十几样。水泥路东侧栽的全是花,主要有芍药、牡丹、月季、玫瑰、蜀葵、节节高、芙蓉葵、百合、鸡冠花、天人菊等十余种。
我和老伴每天都要下田干些农活。
不是在菜园里间苗,就是在菜园里捉虫;不是用自来水管浇菜,就是用袖珍镰刀除草。还用旧竹竿搭黄瓜架,用粗树枝架豆角秧,既节约资金又结实牢靠。养花比经营菜园费工,因为花卉太娇贵。我俩尽量做到适时浇水,适量施肥,疏松土壤,防治虫害。刮风了,得将吹倒的花秧子用树条或小竹竿扶起来。下雨垄沟积水了,还得及时排出。
夏季入伏,太阳如火盆,大地似蒸笼,用旧塑料布给花草遮阴驱暑,防止花儿暴晒致死。我俩退休了,每天都有点事干,也觉得很充实,很乐呵。
我和老伴在家能吃上新鲜菜、放心菜。小葱熟了,薅一把拌豆腐;韭菜该割了,弄捆包饺子。揪几个青椒炒肉吃,摘几根黄瓜蘸大酱。想吃菜包子了,摘点茄子;想吃塌锅了,摘些豆角。除了地上长的,每年南瓜秧、丝瓜秧还爬满西墙。我爱吃南瓜羹,也爱喝丝瓜汤。儿媳说,用咱家刚摘的食材做餐,比市场上买的菜新鲜,也安全。因为她知道,我和老伴从未打过催熟剂,更没打过农药。每年夏天和秋天我家基本上不用买菜,这不仅仅是省几个钱,关键是无污染,吃的是绿色食品。
我和老伴在自家花园就能赏花看景。暮春时芍药开花了,粉红色的花朵映脸庞,扑鼻的清香惹人醉。芍药是多年生草本宿根花卉,适宜在庭院栽培。远在周代,男女交往中就以芍药相赠,作为结情之约。望着一蔟蔟艳丽、妩媚、恬静的芍药花,看着一群粉蝶在花间嬉戏,
有时,还掐几朵芍药花插在花瓶里,放置案头赏玩。“花中皇后”的月季,花期最长,正可谓“惟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享四季春”。在北方,月季从5月可开到11月。我家的几丛白色“香水月季”,微风吹来散发着阵阵暗香。几丛“变色月季”,一株红色深浅不同,一株红黄相间,非常抢镜。几畦玫瑰是去年4月底移栽的,眼前花开茂盛,有的红似火,有的白似雪,有的黄似金,有的粉似霞。玫瑰是爱情的象征,我不嫌玫瑰有刺扎得慌!尤其是对红玫瑰宠爱有加。我俩种下的一片芙蓉葵,秧子半人高,长得很粗壮。每到开花时节,它格外引人注目,原因是它花朵最大,就像一把把小红伞、小白伞、小粉红伞,成为一道美丽的景观。我家的一片节节高,眼下有的开始吐蕊,有的开出小花,花儿宛如各种颜色的小绒球。去年我们种的蜀葵,身段长得比人高,现在也是枝繁叶茂,红花艳丽,粉花淡雅。观花看景老夫妻,一天保持好心情。
我和老伴还随时随地拍田园美景。田里的花草树木蔬菜瓜果,都成了我们摄影录像的好题材。早晨起来,露珠洒在叶子上,像一串串珍珠,我顺手拿起手机,拍了近景,又拍特写。雨后的几丛百合的花瓣上,挂满滴滴水珠,老伴见状拿出手机拍下一段小视频。夕阳洒下余晖,光线柔和,又无风吹,是拍花的好时段。我拍新开的玫瑰,她照冒嘴的月季。在卧房看见窗外一对美丽的斑鸠悄悄落在香椿树上,我和老伴不声不响轻轻按下手机快门,迅速捕捉双鸟嬉戏的场面,记录下这难得的美好瞬间。我对摄影早有兴趣,在一家国企当厂报总编时拍了很多图片在厂报上发表,还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刊登过照片呢。在我的指
导下,现在老伴也成了“摄影家”,不仅会平拍、仰拍、俯拍;侧光、逆光还用得很巧妙,拍的图片非常新颖、漂亮。有时候老伴还把精选的田院美景图片发到同学群或朋友圈,当看到群友点赞,学友评论,她便自信地得意起来,还让我分享快乐,我也眉里眼里都是笑。
我和老伴有时还和亲朋好友聊天小聚。我家平房门外有个长10米宽3米半的大晾台,能打羽毛球,也能跳交谊舞。我俩在晾台西侧摆放了石桌和石凳,还有老式茶壶和茶盅,成了会友品茗的好地方。或约学友聊天,或约战友畅谈,或约文友“理论”,或约工友叙旧,或约琴友操琴,玩得都很开心。我约琴师张正文拉四弦,向他学习唐山皮影伴奏技巧。我练过门,练唱腔,琴师讲要领,做示范,琴音绕梁。因左右邻居白天无人,在这里练琴也不扰民。会友有平台,来者是知己,岂不乐哉!
“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恍若云中世界;云窗中雅听蝉吟鸦噪,方知静里乾坤。”这里离开了城市的烦嚣,没有人声嘈杂,没有机声隆隆,清晨有鸟语,夜来有虫鸣。这里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里才是适宜休闲养老的好地方!
临末,我还想再强调一句:愿守田园度余年!
侄儿来电话说,母亲想我,如果有时间要我回老家一趟。
是啊,我已有一个多月没回老家看望母亲了。往常,我差不多总是两个礼拜回老家一趟,这几乎成了定律。这定律使母亲觉得安实些,因为她能定期看见我和有了可算的期盼。然而,这定律也使母亲多了一些定期的担心与牵挂。在母亲算着我该回老家的日子,从早晨起来,她便和哥嫂们念叨:“我老儿子今儿准回来。”“我儿子该回来了,前晌不来,后晌准来。”倘若因为一点什么,我没有按定律回家,母亲心里便多了些沉重:“我老儿子咋还不回来呢?今儿他该回来了。”“是不是有啥事?不是闹病了吧?”然后自言自语:“他忙啊,别找他了。”母亲的心是很矛盾的,她想让哥嫂们打电话问问,又怕打扰我。我想,这样的日子对母亲来说是很难熬的。
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病了。其实,说病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肠胃不好。若是农
民,人家定不会摆活到医院的。拿了国家钱的人没干什么却是有些娇性,竟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本来是想打电话告诉老家一声,免得母亲惦记,但又一想,一个月很快过去,那时回家再看母亲,不想却还是搅了母亲的心。母亲真的是担心了,否则是不会打来电话的。
回到老家,我坐在母亲跟前。母亲切切地看着我。
“我老叔瘦了。”侄媳说。“是呢!”母亲伸过干枯的手,摸着我的脸。那手有些硬,有些凉。“是不是病了?”母亲仍是静静地盯着我的脸。“没事,妈。胃不好,不怕的。”我说。我如实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母亲。因为我已经好了,告诉老人家让她彻底放心。
可是,我的这句话似乎使母亲验证了她的忧思。
“真的好了吗?大夫说的?”她的手使了一点劲,将那忧思迅速传到我的全身、我的心里,那手更凉了。
“妈,没事,真的。”说着,我抽出手,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步,意思是告诉母亲我真的没事。
但母亲的目光分明在告诉我她还是不放心。
过了两周,我又回了老家。“好了吗?真的没事?”我坐在炕上,母
亲便急急地拉过我的手。“放心吧,妈,我真的好了。”我很轻松
地说。“你可把妈折腾苦了。上次你走后,晚
上妈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嫂子说。我真的有些想不透,上次明明白白地
告诉老人家我真的没事,可她为什么还不放心呢?
“看你的手干的,真的好了?你可要让我放心哪!”母亲的手仍没有松开,另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背上,不停地摩娑着。一双劳作了七十多年的手,摸着一只仅有四十多年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手,却说我的手
干,母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你可不能有一点闪失啊!”我起身要
走的时候,母亲仍是那样切切地看着我说。往日回家,母亲常对我嘱咐的两句话,一句是“路上车多,看别碰着!”另一句是“千万别犯错误,要不,一大家子寒碜哪!”
这次,母亲没有这样说。也许是母亲相信儿子,已不用再那样嘱咐了;也许,此时此刻,儿子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要不就是母亲将两句话浓缩成了一句。
此时,作为儿子的我四十五岁,而再过十年,母亲就一百岁了。
听母亲说,父亲又换工作了。这次父亲在我们小区门口做了一个保安。从我读高中开始,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更换工
作。先是榨油,用一种老式的榨油机,从煮豆子到轧豆饼,大部分工作都需要手动。他每天哼哧哼哧拼尽全力挤出豆油销售,更多的是收取别的农户的一点加工费。那时候父亲虽然辛苦,但收入确实还算不错,我们家成了村里最早的万元户,但这些钱父亲没有用来扩大规模或者盖房子,而是支付了我的学费。
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外地,父亲变卖了榨油的设备,跑到我所在的城市做建筑工人。一段时间后,他把母亲也接来,他们在我所在的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三天两头做了好吃的喊我回去吃饭。可以说,从读大学的第一天,我就没感受到思恋故乡的苦楚。故乡被父亲背在身上,带到了我的身边。
毕业后我的工作不稳定,这个城市转转,那个城市走走,不论到哪里,父亲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细算下来,父亲前后换了不下十个工种,城市也游走了好几个。
及至我结婚生子,父亲又打起了我们小区门卫的主意,成为这里的一名安保人员。但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来我家里住,他和母亲在外面租住着一套小户型的房子,还是时不时地喊我们过去吃饭。
母亲说,这老头子,做事没个定性,工作换了无数个。我知道,父亲不是没定性,他只是想离他的女儿更近点。
父亲就像只迁徙的鸟,有女儿的地方,就有父亲。
老了,没了以前骑上车子就走的便利,只能“蹭”孩子们的车,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整日囚于水泥森林,如饥渴向往清泉,难免要生出思乡的情愫。后来在散步中发现,有一处地方可以略解我思乡的焦渴。这个地方就是菜市,逛菜市成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
我们这座城市的菜市,坐落在东南角,距我所居住的小区有三四里路。市场里除几排塑料瓦罩起的大货棚,更多的是露天空地。每天天还黑蒙蒙,这里的电灯就已经亮如白昼。远近乡村的菜农、果农、渔民、肉贩 ,都 赶 来 批 发 他 们 的 商品。那是成车、成筐、成箱的买卖,是生产者与中间商的交易。如果你不懂门道,去问“多少钱一斤”,人家是不屑一顾的。
与“买点零菜”打交道的,是小商小贩和近郊骑电三轮来卖东西的农民。他们把趸来的或者自家产的东西摆在地下,摆成好多排,像个大集市。各家摊前都放只台秤,主人笑容可掬地招徕着每一位顾客。我所谓的逛菜市,就是逛逛这些地摊,体味一下浓浓的乡情。
地摊上的蔬菜都带着露珠,新鲜水灵。我就像走进了自家的菜地,拣着自己喜欢的,任意选择。买白菜,我选未捋叶的,当场打理干净。买萝卜,我选根上沾土的,就地摩挲光滑。西红柿捏着结实,必定沙瓤。黄瓜顶花新鲜,准是新摘。在这样的菜摊上行走,我觉得扑面吹来的都是田野里清凉的风。
走过肉市,老远就听到了砍刀剁排骨的咔咔之声。如今的肉市,卖肉的少了镇关西和胡屠户那样敞怀露肚的埋汰汉,多了手艺利索的小媳妇。她们笑容妩媚,态度温婉,让你走过就不想空手,多少也得砍上一点,不然就觉得对不起人家的热情。
来到鱼市。冰冻鱼虾码成垛,怕的是单摆单放融化。鲜活鱼虾养在箱里盆里,噼里啪啦在水里游。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哥,面前铺一张塑料布,上边倒了一堆活蹦乱跳的草虾。我情不自禁走过去。老哥笑,露出满口白晃晃的义齿:“老弟,让你赶巧了,起早刚网的,拎一兜吧。”我蹲在虾堆旁,眼前立刻出现了小时候在河沟里光屁股打鱼摸虾的情景,“谢谢。”二话没说就称了二斤。
最后来到卖水果的地方。粉红的鲜桃,金黄的鸭梨,红的、黄的苹果,远来的橘子、香蕉,果香馥郁,沁人心脾。一位卖桃少妇盯我几眼,忽地走到我身旁,“您是刘大伯吧?您回村时我见过您。”我愣愣地望着人家,咋也想不起她是村里谁家媳妇。“三喜过来,刘大伯来了!”她丈夫闻声而至,我立刻恍然大悟:他叫崔三喜,他爸是我的学生,因为复课,他爸还带他找过我,几年不见,他都娶媳妇了。没想到在这里,我还能遇到村里的乡亲。以前骑车回家,我常去他家桃园里玩,早春看花开,盛夏看桃红。
告别三喜小两口,我走出了菜市场。到这里每逛一次,我觉得就又回了一趟故乡。
母 亲 的 牵 挂母 亲 的 牵 挂□ 解占久
愿 守 田 园 度 余 年□ 王树国
偷 花 生偷 花 生□ 黄卿
逛菜市
□
刘振广
父亲换工作□ 刘超
Top Related